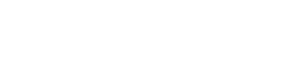共同体的悲喜笑剧:从政治谈话性节目与全民大闷锅谈起
观察当下 台湾 的 政治 认同冲突,迎面向我们的感觉经验冲击而来的,正是某种粗暴的集体情感形式。透过媒体的再现与 影响 ,我们看到在民众普遍对于政治感到焦虑莫名的当下台湾,在个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现实,被行动的激情所驱迫,甚而失控流泪、大笑、愤怒、焦虑或者转而静默承受之时,那为众人所期待的政治空间,是否因此而向我们敞开?
台湾政党恶斗的夸张场景,浮泛的政治论述、报导,到电视政治性谈话节目中深具煽动性的言论所共同展演出的戏剧性景观,其仪式般的感染性,皆不断进行着召唤民众对政党、国家、族群意识 进行在行动与情感双方面的认同工作,以堆栈形塑政党私自欲求的权力资源。这种反复在台湾民主过程中召唤民众激情的情境,正是Rancere所说的,“感觉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的场域。它激发集体参与的激情,甚至是内化到一般民众生活的情感之中,透过感觉分配与外在化的 社会 形式反复情感召唤,两者间的交互循环,不断进行各种检查、夸大与界划的动作。它不仅仅造成实际政治运作中认同与排除的 问题 ,也造成民众实质的情绪与情感上的伤害与压抑;并且,更根本地,它重新规划了我们对政治事务到日常事务之间,各种感觉与理解的范畴,意欲将我们的感知,固着于某种僵硬、沉重的感知经验形式上。感觉分配的形式僵化,导致政治性空间的可能性,逐步僵固成为由一群占有权力位置与论述权威的国家机构、政客、媒体,甚至于专家学者论述形式所掌控操弄的封闭政治(politics)。这种感觉的僵固形式,向我们揭露既有政治意识内部激情的基础;这个无可抑制的情绪基础,正是一个共同体的问题。
而媒体,作为一种有力的中介物,在每日毫无厌烦的社会政治新闻报导,以及政治谈论性节目滔滔不绝的横飞口沫之中,发挥着影响力。倾向同质化的政治意识与论述,透过媒体中介,进入民众的认知与情绪中,召唤再捕捉,将你我融入一个不可见的,由同一认同所形构的共同体场域之中;因而媒体在政治性的窄化或是划界以自我封闭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样的,作为有限政治感觉分配与外在化、具体化的有效中介(或是转达物mediation),媒体,在政治操作的召唤过程中,亦赋予不同一、差异的个人感觉在政治场域中现身展演的机会与能力。充斥在那些节目中的煽动性话语,在观众生活实践中所引发的行动,使作为符号与意识形态消费的媒体节目,成为互涉的中介,而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传播 ─它制造其响应者,但是这些响应者拥有自己的声音。因此首先我想讨论,这种在共同体的感觉分配过程其可能的内部复杂性、矛盾构筑以及断裂,如何在此媒体的中介过程中展演变化。
我试图以普遍的中介的媒体形式,即政治论谈节目和「全民大闷锅节目」为 研究 对象。从台湾政论性节目激化政治认同的沉重激情的过程,以及与其对应而生的娱乐拟仿剧节目:全民大闷锅节目,所企图引发的笑的情绪,自两者之间的对照关系,寻找矛盾构筑的暴露。并且,我希望能够进一步讨论这种暴露,在开启政治性空间的层次而言,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感觉分配形式如何能够不被固定?同时,这些无可避免的情感欲求因素,在感觉分配的形式中介过程之中,本身是否可能产生变化与主体的能动性?或者这些情感欲求在政治过程中,其意义为何?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必要的情感需求?
一、政治的美学体制(aesthetic regime of politics)与感觉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首先,我的讨论将先从Ranciere论述中的美学概念出发。
从当代的 艺术 运动与文学史 发展 ,尤其是前卫艺术的政治性宣言,与其在艺术与生活之间所试图进行的政治性突围过程中,Ranciere离析了“艺术(art)”之所以能作为艺术,与美学(aesthetic)之间的差异,以及两者之间紧密交织的关系。对Ranciere而言,艺术依赖于再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representation),同时也就是一个诗学(poetic)的体制。在此场域之中,再现的(representative)、或是仿真(mimesis 与imitation)扮演着关键作用,统筹所有做、作、看(或听)的感知行动与判断方式。仿真,既是诗学体制的外表,也是诗学与现实之间的阻隔;艺术(arts)便是藉由这种阻隔定义出其特殊的范畴,而非仅是相似与模拟(resemblance)的综合。总而言之,此再现与诗学,如同做与作方式的配置里的皱折( fold)1,她所体现的各种(艺术)形式过程与类型的分别与阶层,是一个称为可见性的体制(a regime of visibility),相关于一切可见、可感的做与作的形式,包含了各种已完成的作品或是生产,他们一同展现成为一个共同体层级化的视野。
而美学,不同于诗学的体制,它以存有的可感样态(sensible mode of bEing)为基础,将自己与艺术生产分离开来;它既不是什么感觉的 理论 ,也非艺术爱好者的品味和愉悦,而是关于一种艺术客体的特殊存有样态(the mode of bEIng of the objects of art)。
….在这个美学体制里,艺术现象以感觉的体制(regime of the sensible)为皈依。然而,此感觉的体制却总是与其原初的联系相解离,并为一种异质的力量所填充。这个异于自身的思想形式之力量:是以未产出者来辨识自身者、将知识转换为非知、理性/真理(logos)相等于感性/情感(pathos)、或是非意图的意图…等等。这个感觉的体制的概念总已是远离自身的,分歧的,那思想形式的场所(locus)亦然;而这正是从一开始即形塑了思想形式之美学模式的艺术一致性的核心。2
Ranciere认为 现代 文学与艺术运动揭露了上述这个美学状态,并且此艺术的美学体制进一步破坏了艺术在艺术法则与社会法则之间的阻隔,将艺术自再现与可见性的法则,以及仿真的界碑中解放出来;它同时建立了艺术的自治性,以及艺术形式与生活用以形塑自身的那些形式的同一性。Ranciere指出:此美学状态(aesthetic state)是一纯粹的悬置程序,是形式经验它自身的时刻,并且是一个建构与 教育 特定人性式样的时刻。
此美学体制的登场,其实与现代性(modernity)有着破碎暧昧的关系。她关联着现在如何让过去重新登场(restage);它决定并诠释什么使艺术之为艺术,包括何者是现代艺术亦或不是,其内涵如何,以及艺术造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个不仅仅是艺术的,并且同时涉及了现代生活的美学状态,提供了我们某种共有生活(communal life)的律动,以及在时间与空间上共享的生活形式。它向我们提出一个等同于艺术终点3的,“对于共同体生活的认同”。
Ranciere进一步说明,在政治(politics)的核心里,本就存在着这种美学,而且此种政治与美学的关系,并非班雅明(Benjamin)所说的 “政治的美学化过程(aestheticization of politics)”。Ranciere所指的这种美学,并不是那种由热切追求艺术的意志所指挥、视人民为艺术作品的政治意识,而是更接近:一个属于先验形式的系统,它自我决定以何种形式向感觉经验呈现自身4;因而它得以进行着空间与时间、可见与不可见、言说与噪音之间的界划工作。美学体制在此几乎就是政治(politics),规划可感与不可感、可说与不可说的关系、谁具有这些能力、以及空间的所有权与时间的可能性。它不仅是设置、安排了“一个场所”(place:总是熟悉的、亲密的、有限的。)”,同时是一种Ranciere称之为感觉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的过程,一个感知的自我证成系统,一个共同体(community)。此共同体(笔者按:由共同感觉所构成之身体),总是即刻呈现出在其内部的普遍规则、个别位置与部分(parts)的界划,藉此建立起普遍同一且同时的感知分享与排除。这些位置与部分的分配,立基于那些普遍的空间、时间、活动形式样态的基础,亦引领着自身的参与方式(participation),与每个做为其一份子的参与者。
这个政治的美学体制,如同一个光明的、父性的神(,无庸置疑,是绝美的);以照明的力量规范一个不可见的秩序世界,以及一个共同体,召唤我们成为它(可以称得上是,不断出生与窒息)的孩子;崇拜它取悦它,甚至可以奉献我们的生命;但是它亦同时是一位母性的神,赋予我们可以生而为人的恩赐,让我们恣意地感知与生产创造玩耍各种形式,印证它的丰饶与包容的力量。即便,它本身只对感觉经验现身,仍是我们共同的信仰或是想象,所召唤与投射出的“神”。
二、神的祭典:美学化的政治与政治的戏剧场景
在一般状态下,可见的实践形式常常皆已为某美学体制所附身,同时成为我们感觉经验的召唤者以及对象。特别要注意的是,可见的形式在Ranciere这里并不是只就一般艺术的实践而言,而是指所有作与做的方式与产物。而在这样召唤特定感觉释放后,感觉经验再返回召唤者的过程里,我们对形式本身的感知便成就一种认识的教育,不但使形式本身那些未能向我们的感知展现的不可感知者,长久地被封闭在形式内部或者我们之外,我们被此特定感知经验召唤─复返的强化过程,亦逐渐驯化与规范我们对世界感知与探索的某种原始模式。这个于不可见处运作的美学体制,总是要透过各式作与做的形式,以及我们的感觉经验或是情绪来同化我们。
而长期以来,台湾政治斗争模式、论述构成,在解严、媒体的解禁之后,在愈益浮泛的媒体报导,与电视政治谈话节目中,逐渐激化为深具煽动性的言论、画面,以及发生在不同分类范畴的争斗场景。他们所共同展演出的戏剧性景观、重复的仪式场景,皆不断进行着召唤民众参与政党、国家、族群等共同体认同,以生产政党、媒体或是社会体制所私自欲求的权力资源。这些外在化了的认同与激情,透过特定语言模式、书写论述、符号展演,以各种可见的社会形式出现。他们召唤与建构了一种共同的感觉,这个共感又再转以不同的形式实践出现;这反复在台湾民主过程中,召唤民众激情的情境,正是Ranciere所说的:政治的美学体制,而且是美学化的政治现象,在每日不断建构“感觉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的场域。感觉分配外在化自身为可感的形式呈现,总是指向一个特定的认同模式,并以外在化的形式再反复向感觉召唤个体以形式的实践再强化感觉分配的机制。感觉分配与形式两者间的交互作用,持续共同体的实践。讽刺的是,从特定共同体视野外来看此热烈的景观形式,它呈现的总是一种扭曲的美,一种骇人的神圣感。(或许是因为那神圣的脸孔因强烈召唤而越来越逼近?!) 透过感觉经验呈现自身的,原来是一张具有恐怖之美的脸孔。但对于沉陷于特定共同体激情内的一份子而言,或许它仍是美得足以让人为其赴死。
在这个不断生成与安排自身的政治美学体制内,只有特定的事务可以特定的方式被感知、理解、可(被)见与可(被)说,以此维持我们对这位共同神只的无上崇敬;像在所有敬神的仪式场合里那样,(所以,请勿胡乱笑闹!)。此“崇敬”所造成的偏见,持续召唤更为纯粹与强烈的情绪:包括牺牲的骄傲、被护佑的喜悦与消灭敌对的热情,以及更为僵硬固着的理解与排斥。在台湾进行着如此白热化、鲜明、僵硬的感觉分配,和共同体的斗争剧码,幸而,或许因为仍然立基于更根深蒂固地、对平静社会生活的惯性,或是碍于法治规范的规训,当下的台湾社会,尚未,仅仅是尚未,发生过于血腥暴力的惨烈牺牲。但是,小至对劣质选举活动、具相同激情认同的团体暴力、不当教育体制、 经济 不景气、 新闻报导论述的自以为正义、热血的习以为常,或是习惯性采取特定的情绪模式,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暗自遵循不与不同政营的邻人讨论政治话题的社交合谐法则,或是,莫名地厌恶某个毫不熟悉的公众人物、对非己者的问题漠不关心…,大到对那些自圆其说的所谓正义、伦理与民主激情的认同、叫骂或漠然。在这些形式与情绪的仪式场景中,是否有什么被牺牲了?以致每个生活在台湾的人都感到怅然若失、无法忍受?
既然情绪表现为感觉经验的说明,通常便具有一种形式化的规范性(regularity), 此规范性立足于一共同体的普遍性上,响应各种外部形式刺激以合宜的行动。 也就是说,除了透过言说、身体行动、展演、艺术创作、书写工作等等,人的情绪表达,甚至属于更初步的感觉分配过程,受到美学体制的管理(police)。这个过程就是一种美学政治的实践过程,许多时候,这些情绪与形式 内容 ,已远远超越戏剧里洒狗血的幻想剧码所欲达成的激情效果,完全消灭了仿真(mimesis)的阻隔,成为难以面对的现实。于是乎,像所有古早的文明传统那样,我们确实地以盛大的戏剧表演仪式,膜拜共同我们的神。
三、奢侈的仪式与不敬者?
(一)政治性谈话节目与全民大闷锅
社会形式与文化形式,以及那些具有可见性的可感形式,都是作为共同体的呈现,也是共同体内分享者的生产。共同体的个人将对沟通和共有的情感,投注到形式的外在化实现中;这些形式,便是媒介。媒介既是Nancy说法中构筑在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媒介、社会形式,也是Ranciere的皱折、纠结(knot)或悬置,是不平坦连续的表面也是他者的空间所在。媒介既是做为社会文化,或共同体的形式,便具备制造对共同体进行想象与感觉的能力。
在现代台湾社会,电视媒体仍然是最普遍重要的一种媒介,她具备了包含多种艺术形式再做转达的能力。台湾的电视媒体发展在解严,媒体开放与有线电视普及历程中,明显的,逐渐吸纳了传统意义上最有力的剧场形式的政治空间;八十年代社会运动中惯用的戏剧动员手法,如今也已和电视媒体动员相融合, 形成一种有力的动员形式,因而,其传播能力的效应反而成为许多问题的所在。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他讨论近代社会对共同体的想象建构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当时报章媒体在共同时空感建立上的影响。而当下台湾媒体的影响,则是共同体建构在台湾的重要因素。我试图从一组对照式的电视谈话节目,来比较与展开做为媒介的形式,在共同体的情感分配与激情中,如何引发与影响我们的感觉经验。
(二)政论性谈话节目
若从共同体的过程,感觉形式的实践,与共同体自身的流变挣扎的角度,来看 台湾种种政治操作的感觉分配方式,最为明显可见的,就是在公共媒体上,政论性谈话节目形式展演,所进行的共同体之间的斗争 (,暂且不论在台湾,这种共同体的范畴,是否等同于单一国家认同),与巩固自身的动作。政论性谈话节目,看似为一种严肃的政治场合,参与来宾多数为相关政治运作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政治名人。节目中所进行的议题讨论,绝大部分是围绕在最新的新闻报导焦点,以及情绪煽动性最强的公共议题或是政治议题上。所有的讨论 由主持人调配在一定的问题范畴中。讨论模式通常是在一个大议题下,进行多方展开的问题讨论;主持者主导所有的提问,由不同领域与不同政治立场的来宾响应问题,或是提出事先已经准备的议题相关资料文件,左证说明响应,并且开放观众电话call-in的机会,让一般观众也能公开地提出个人的政治看法与意见。在理想的状态下,这种政论节目的确可能提供收视观众,针对于一个社会政治议题,多方专门的政治性观点,以帮助与打开、扰动可能固着的个人政治偏见,而不是仅仅提供一个既定答案或是 总结 。同时,开放给观众或是参与者一个公开发声的政治空间,增加一般民众实质的公共政治参与机会,以及鞭?时事,以进行政治性的辩证工作。但是事实上, 目前 台湾的政论节目,并不是如此,甚至绝大多数时候是朝向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这些政论节目主要的特色在于:1.欲型塑整体同一偏执的认同态度与立场,2.特定固着,可以预期的言说模式与逻辑,以及3.吊诡的娱乐性或是政治性。
通常操控节目流程的,是主持者主导的问题,但如同当下台湾媒体记者的问题那样,绝大多数是偏颇、预设立场与不是提问的问题。因为所有可被言说与接受的响应,都已在那些提问中被解答了,或被预期的。这种几乎是自我肯定的问题,绝对不是任何真正的提问,它只是一种感知认同的再肯定、再确认,并且是以问号的收尾来建立问题的身份。几乎所有台湾政论节目都是为特定认同群体而开设的,它的诉求对象常限定于特定认同群体;但这件事实本身并非问题所在。通常,政论节目的主持人与来宾,看似客观多元,事实上却有同一的政治认同,或是态度认同。多数响应的言论,主要是基于情感与认同激情的响应,或是基于专业的公众媒体礼仪的形式响应。即使是最激烈的口水激战,背后仍然是相似手足之情的大力相挺。突然现身的异己call-in观众,总是徒然,总被节目中所有人当作不曾出现。节目中发言者的激动言论,则无非是在积极召唤收视者对同一认同的情绪响应,试图在声音与影像无形的传播中,为共同体大合唱。甚至,当下的台湾政论节目已经演化为政治动员的序曲,配合着新闻报导,激化普遍民众的情绪;无论是认同或是愤怒,引发群众为共同体现身、发声于镜头前、舞台之上、于公开可见的媒体之内,似乎已是这类节目的职责所在。无论是利用公民理性或是传统伦理道德,或是更甚者,某些政论节目召唤“个体本身”成为共同体的实践形式。透过媒体的再现,我们见到的那些在街头上的激动身影,通常也不会再是平常在路上会遇到的,过着平凡生活的老先生,或是帮佣,而总是做为共同体表征的醒目尸体。
政论节目的所谓政治辩论,与其可预期的言说论述模式,无非旨在制造一种“感觉上”的判断程序,引发极简单的是非题式的判断情境,旨在提供一种经历理性的判断过程的幻觉。节目中那些奇怪的问句,难道不是在可见形式最表层的表层,最靠近的邻近,向不可能抵达的远方致意的一个微弱、亲昵、自以为了然的手势吗?而一个真正的提问却将会带来尖锐的危险,是容不下任何无力的手势的。节目的共同参与者(具同一认同的观众与节目来宾)必然的、一致同意的响应,愉悦、满足了所谓的判断者,对于自身仍然保有理性能力的妄想,并且替代不可见的共同体神只,给予她的每一份子庄严的肯定。(看,这是多么亵渎的一种僭越!) 或许,这些所谓判断者早已被剥除进行判断的权能了,因为,在共同体之内并没有所谓超然的判断,所有的沟通早已是分享的激情,并仅仅是激情,这沟通终于空无,因为缺乏任何异质与不一致者的现身,其分享几乎仅是分配后再重复自我吸收的过程。
或许极端地说,并没有纯粹的知识、 历史 事实、宪政 法律 或是逻辑理性,可以在共同体内部做出公正的判断;或者说,在这种仅有内部同质的状态下,以上那些也难以被感觉的分配、认同与接受为判断的依据。在我的感知中,也许,绝对的判断都只能发生在共同体的边缘或外部。在共同体内部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判断,或是仅有难以判断,更遑论所谓正义在此的意义!尼采说的更为直接讽刺:正义仅仅是一个感觉5。此正义只属于共同体自身的决定,因为在同一之内不会有冲突,那些冲突都早在可感知之前被加以抹除,仅剩下必须自圆其说的形式(,像对不识相的call-in观众那样)。若面对的是来自另一个共同体的判断冲突,也就是当我们突然隐约地感觉到相异的认知时,在此,正义的判断则表现为:对共同体内部不安情感的安慰与消除,将思考与沟通外界未知的大门暴力地甩上,甩在所有试图透过收视政论节目,试图将孤单的自己连结出去的,每一个作为共同体一份子的人们的脸上。在感觉与形式如此僵化、暴力独断的中介上,每个人事实上都不再能够与他人有所联系,只能转以言说相同语言、急迫于一起行动、与众人一起前进以求慰藉,至于这些言说的指涉与行动的方向,是不被注意的。
同时,也再没有比政论节目中的主持人与来宾更为称职的演员、甚至是双簧演员了!所有的发言与提问、证明,仅仅是试图制造一个开放与提供判断意见的公共场域的假象,一出真实戏剧。它不仅是假象与虚构,还是呈现给一个高于政党认同群体的共同体,及其内部的每一份子的娱乐剧码,而非仅仅限于是政党认同间的斗争把戏。它总是试图收拢,愉悦观众的情绪,因为收看、参与其中的观众,并非皆具有政党的认同,或是可以单纯地以族群身分来做区分。尤其是对缺乏过去共同历史政治的深刻经验的年轻一代而言。事实上,喜爱收看政论节目的观众群,常常要在特意安排在同一时段播出的各台政论节目之间选择收视,因为它要进行忠诚认同的确认与划分。但事实上,有一些观众是跳跃式的收看。无论如何,政论节目整体呈现的特色,总是指向一个共同的僵固形式,但为何必须如此?倘若做为媒体中介的政论节目达成了任何的沟通,在这类僵硬的表述里达成的,也仅仅是孤单的一般民众,(特别是社交娱乐方式贫乏,社会能见度低的中老年男性),面对着电视机进行政治激情的释放。我们没忘记,或是要需要再次提醒所谓政治死忠的虔诚者,政论节目不过是一个节目,一场秀,而非政治。
对共同的激情,呈现在政论节目的形式中,为我们演出激情横流的戏码。而其中共享的人们,都必须顺从那带来无与伦比合谐与快乐的游戏规则,一起跳着手拉着手的圆圈舞蹈,感染与包覆在崇高的愉悦当中,最终升天。如同米兰.昆德拉在<笑忘书>里说的那样,与大家一起跳着手拉着手的圆圈舞蹈;但是,
欢乐在不断地被重复之后,时间的存在与时间的无穷性也因而遗失了,最终将如同在“时间的荒漠”之中那般,令人窒息。然而,一旦被圆圈所拋出,便只能不断地坠落,再也回不去那个令人永远怀念的,圆圈的喜悦。
有些时候,对于某些人而言,政论节目甚至仅会起着最低限度的作用,带出某种阴惨的、出气式的、自我安慰式的痛苦与自怜的愉悦,这类感觉相似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LITOST:是在爱的认同之中,一个人突然洞悉了可怜的自我而产生的痛苦,然后是一种想要报复的欲望。
假设,试想一个赫然发现了政论节目或是其它固定单一的政治表现形式,并不代表任何属于“台湾”认同,却寻求共通的复杂个人,政论节目只会让他感觉到共有与爱的形式的共同体6的不断失落。这个个人有时便会走向这样的一种情感,litost,因为认为自己无法被爱、不值得被爱,或是无法信任共同体的爱。于是在不可避免的认同拉扯中,他或许会以可笑荒谬的方式报复共同体以及伤害自我,以试图测试这个认同的安全与爱,或是试图脱离、弃绝或被弃于共同体之外。我们是否可以想象这样的个人?一个矛盾地相信共同体与政治,而一直在试验彼与此的个人?这似乎是个可以再讨论的问题。
政论节目如此公开地给予的正面情绪肯定召唤、宣泄机会、对共同敌人的否定、扭曲与讽刺谩骂,所引发的肯定情绪,满足激情的响应,激励与取悦着同一共同群体中的每一份子。但是,为何它会形成某种社会作用呢?我们是面对何种失落,才会需要它的补充,以及许许多多其它形式的补充?(BBS政治板、政治抗争英雄、激烈抗争、以至于中文版南方四贱客、全民大闷锅节目等等)或许正是因为,政治参与感觉与实践形式的不充足,和共同体沟通感的匮乏。生活在台湾的人,在复杂冲突的国家认同、历史认同、政治认同之间,承受着共同体认同之间的苦难挣扎,是否如此会加剧对一个强有力统合的共同体的期待?甚至是否因而会奇怪地发展为,个体对所在的共同体进行情感的奢侈消耗,狂热于同在一起的爱的关系,而成为投注于僵化共同体的形式,且演变成为消灭共同体本身,以及各共同体之间的动态挣扎?企求一个僵化固定的斗争景观形式,以求经验感觉一个统一、纯粹的、完成的空无整体?或者是,藉由奢侈地消耗激情以献(现)身于祭台的热情,(由于没有肉体的死亡,所以能量更是源源不绝),将个别的死亡染布共同体,以求共同体不可能之完成?但实际上,如此却是转向杀死或离开共同体本身,以僵固、贫乏的爱之形式,进行对连系着不同个人的共同体的亵渎。
转贴于论文网 http://www.lwlm.com与口号即等于爱的深刻情感、化身蓝绿红等颜色即等于 政治 性的理解与参与;或是单纯地以为走上街头的游行抗争和占据论述权力的舞台都是基于一种自发却单一的、共同一致的、无差异的情绪与认知因素。 这些似乎都是以某种暴力简化了个体的可能,以及忽视共同体内部的对抗性质。而且将美学化了的形式与感知做了一对一的关系固定,将形式与感知意义混为一谈,扁平化了对实践形式的意义、并简化了人性(即情绪感知)的复杂,忽视了个体于其中径行虚构扭曲伪装游戏凑热闹玩笑自娱无心等等因素。难道“我”加入街头游行难道不能是为了自我娱乐、运动或是凑热闹吗?即便同旁人一样高喊口号,也并不表示我与旁人必然共有相同一致的理念与动机。我可能仅仅是想融入与大家一同的乐趣与感觉分享罢了,而非是任何论述形式所欲加之于我的感知的任何神圣性的诠释。
这类亵渎,以及僵固的美学形式对共同体所进行的破坏,正是透过固着形式与感知键结关系、以及感知本身受种种暴力压制安排而成的钝化与简化来达成。以致在看似华丽奢侈的献祭景观中,我们竟矛盾地感觉难以忍受那种单调无趣、贫乏、重复激化、压抑的感知与形式,而至感觉疲乏,逐渐形成对政治的冷漠无感,摸不着头绪,而毁坏了我们对理当丰饶的“我们的神只”的信仰。普遍而言, 台湾 政论性节目以及相关新闻媒体,正在进行这样的破坏工作;媒体作为相当僵固却有力的一种美学化形式,由于其中介性的强大召唤力与包裹携带能力,它总可以轻易安排布置出一个盛大纷乱的展演场景,酝酿一场超出召唤预期的 社会 游行抗争,甚至无须也无法对此负起任何实质的责任。
可是我们不能忽略任何可能。从另一方面来说,政论性谈话节目,做为政治(politics)论述生产的中介形式,它所制造、提供的、可以重复强化单一论点与煽动情绪的言论,即感觉的再现、外在化的过程,不可否认地,仍然提供了一种言说形式作为个人联系政治性的媒介与能力基础。那么,从感觉发配所延展而生的这种言说行动展演与机动性语言,透过民众重复言说、自我挪用为描述个人生活经验的政治性语言形式,藉以自我赋权的过程,是否也可能从这类言说的内里,找到解开封闭政治论述的局限性,朝向政治性发声的可能性?让我们有机会说出既有僵化的政治论述方式,所无法说出的,展开各种尚未可见的绉褶空间?甚至,要回头“发现”那些固定的言说形式与欲外在化自身的美学体制本身,呈现了怎样的矛盾、抵抗与可能性。
四、美学体制的内在矛盾
(一)Ranciere的讨论
一个政治的存在(political bEing),便是指一个(可)言说的存在(speaking bEIng),也必是集体性的、处于共享之中的;他也就是必须在那些对共同体而言,普遍的基础条件上是可(被)言说的(因而也是可能沟通的),否则,便不是一个作为政治存在、属于共同体(community)的公民(citizen)7。进一步地说,既然,属于共同体的一员,必须以其可见、与可言说的外在化形式来证明这种身分的达成。在Ranciere的政治的美学体制,或是感觉分配中,虽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关于形式实践( practices)的矛盾 问题 。
作为一个先验形式的美学,以及自我证成的系统,她都必须依赖外在化、物质化来完成自身。这些具体化的形式与那先验的美学形式之间,具有相互证成,但是却内含相互矛盾的关系:美学的实践(aesthetic practices)与 艺术 的实践(artistic practices)─也就是诗学(poetic)的问题,便是美学与共同体朝向自身完成,以及不断场所化(placing,即安排、配置内部),场景化(staging)自身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矛盾所在。她的症结就在于艺术的实践形式里的模仿(mimesis或imitation)原则。
Ranciere认为,就像在诗、剧场舞台和书写中那样,先验的形式(不朽的神话、幻想以及语言的 影响 等等),与具体化的形式作/做法(文字、身体与公开的活动),分享了同一个场所,彼此之间却仍可能出现矛盾或对立,打乱了原本分明的认同区隔(无形与有形、活动与时间等等)。因为在身体动作的展演中,可能分裂自身(在意义、认知与感觉上)为二,进入自我对抗的状态,或是在文字的任意流动中,也可能生成缺乏合法性的读者共同体那般。包括那些发生在十九世纪后的小说、前卫(avant-garde)与 现代 艺术的 发展 中,各种混合交错的艺术形式呈现,以及在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跨越,创造了政治的(political)接口;它同时包含了艺术反思所进行的政治性介入。因为此接口撤销了在再现逻辑(logic of representation)中的双重政治内在,这双重的内在包括:第一个方面 再现逻辑将艺术模仿的世界,与攸关生死的世界加以分隔;另一方面,其阶层化的组织,却也形成了与社会政治秩序的相似性8
我们可以发现,从第一方面而言,它违背了呈现美学体制时,必须破坏阻隔现实世界的仿真的原则。但另一方面,却违背了可见性体制(即诗学体制)欲在现实与艺术形式之间悬置距离,以达美学状态的特性。
由于美学体制在向感觉经验呈现自身时,所必须依赖的实践形式,也就是诗学、作与做的方式,早在基础上包含了背叛。因而,在可见性的形式呈现美学体制时,会产生不可预期的皱折与纠结;所有美学化的可见形式,必然会伴随不为美学体制或感觉分配所允许知觉的阴影与空间,即那些在共同体内被抹除、排除、不可感知之物得以潜伏、流动之处。
尽管如此,Ranciere似乎却并没有清楚说明这些皱折的空间,如何可感或不可感,或是可能如何造成感觉的影响变化?其与感觉的主体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共同体内在的这些悖反基础,对理解共同体而言,意味着什么?共同体的沟通与诗学体制之间关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可能坦然以无意识的范畴,无感之感,空无或是非知的命名来简化说明它的影响。但Ranciere确实提醒了我们,任何可感形式,都不能被简单地被视为“涉入政治体制”的特定方式,或是能指定出在形式和美学(政治/生活)之间决定区隔的规则,或定义出共同体必然是如何。尽管,这些可感形式的确保持了某种 历史 的不变性,共同体却仍是不可能以僵固的形式完成自身的。因此,Ranciere认为我们必须被解开的症结在于:在决定什么对共同体、形式的可见性、和其结构而言,是普遍可接受的问题中,感觉分配(共同体)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虽然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任何简单、既定的答案,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那些隐密的绉褶,必会随时见形式的扩展而增加,共同体那“不可能完成自身”的实践,不会是任何单一固定的,可预设的形式:她只能是持续与自身相远离地,复杂联系地关系化的过程。或许,如政治性那般。
并且我想强调,当我们听到或是提出这类问题:「为何某些荒诞牵强的媒体论述,或是扭曲是非的说法仍可以获得某些人的认同?」。这提问的可能性是什么,或许是需要在获得响应前可以再悬置与思考的。这类问题是即将分歧展开的提问,亦或是将停留在情绪表达的陈述阶段?任何一种认同者都可以对非己者提出同样的问句,句中是否实时地标示出某个主观认同的固定位置、进行了特定认同的价值判断,同时指出了某个对指认者而言,无法理解与感受的未知?更或是其它更多意义与问题?暴露出一个美学体制,或是感觉分配的问题以及其界限(limit)。也许,那些可能的奇怪愤怒与似乎站在更佳位置的道德同情,都在消灭此类问题的可能性;如果可能,是否可以自此试着以想象力与感受来仿真他人、或创造一个他人?而不是以有限的感觉将他人固着或当成尸体。既然没有任何人可以“是”另一人,那么我们就只好试着当自己,当无数可能的自己,试着成为一个人,并且从作为普遍的人联系与那些不可及的他者的共同关系,以期打开一个共同体或是政治的界限。
在Ranciere对政治的美学体制的讨论里,很重要的是,他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无形式,不可能直接感知的,但潜伏在每个可见性形式中的统治体制的概念。(虽然对这概念的理解,也必然已经是抵达了可感知、思考、与言说的形式之中。) 他同时也提示了这些可见形式(做与作)的方式,即诗学的体制与此美学体制之间的关系,来把握可见性范畴与那不可见者的“之间”。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透过我们感觉的原始力量,去发现去揭露这样的“在之间”,而不是落入另一个企图以某种放弃可感知的存有状态,而将自身拋掷于“自身所感觉虚空处”,这样一个以消弥感觉差异作为同化方式的美学体制里。美学状态所依赖的形式悬置,既是特定人性样式教化的起跑线,亦可以是自那条细微悬线于时空中之缝隙 不断地溢出其它。 从此悬置还不“是”任何一种以二元对立所界划的任一方之处,尚未此亦未彼的时空状态,是相互矛盾、不可达到,却又能不断贴近不断创造无数联系企求不可感者的现身,此共同体(美学体制)亦仅能以这样的过程成为自己。这种理解,相当接近于Jean Luc-Nancy对于inoperative community的思维。那么如何可能进入这个悬置的瞬间?如何尽可能地处于可感形式的边缘呢?
(二)全民大闷锅节目
在可感知的一面,由于台湾政治恶斗,总是倾向以政治神话的叙事与神圣化的崇高景观,来召唤民众(对国家和政党)神圣、严肃、忠诚的认同感情;这种无可避免、沉重如钢铁的激情形式,拖曳着我们盲 目前 进,越来越多人因为不可承受,而伤了、累了、甚至放弃了,而在情感上转向寻求治愈和纾解这种伤害。因而,或许并非偶然,许多非正式、非政治场域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谐讽的作品;在最为普遍的台湾电视媒体上,也逐渐有了像台湾版配音的南方四剑客卡通(1999年)和全民大闷锅(2000年),这样的娱乐性政治讽刺拟仿节目出现。
<全民大闷锅>节目一开始,即以仿真、嘲讽政论节目的型态出现,甚至模仿了政论节目的现场布景 call-in情境,包括画面上的call-in号码、观众call-in的仿真,到屏幕画面的分割等等。节目中的拟仿表演对象,通常是那些在一般政治领域与公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最常曝光、知名度最高的名人、艺人;最被强化、印象固着的社会事件与现象;以及一般生活领域中,最为典型、特定的话语模式。刻板固定的人物、事件与话语模式,正是大闷锅最重要的操弄资源与进行幻想的基础,也是它意欲抵抗者。闷锅的拟仿表演正是凭借着一般新闻媒体,社会论述权威、逼真性,以及现有政论节目所铺陈、建构的表层认知构架,才获取它得以扭曲的对象。
<全民大闷锅>擅长以丑怪夸张的扮妆、表情、声调,以及挪用、拟仿政论节目与社会现象中常见的固着话语模式,来进行扭曲变异的吹泡泡游戏,吹破种种专家名嘴与政客,假理性、正义社会公理之名的虚浮言说。藉由挪用、并置、扭曲这些固着的话语形式,偷渡闷锅节目本身用以吸引观众发泄情绪的伎俩。
同时,闷锅节目发展出以特定场景框架,进行想象式拟仿的小单元剧,以挪用的刻板形象进行想象场景的展演,交互穿插在做为主要节目架构的“仿政论节目”模式中。
整个节目进行,几乎主要拷贝自一般政论节目的方式,明显地,特意经营出政论节目娱乐化的真实效果。依照个别角色设计誊写的夸张台词、意见发表与表演,总是特意以现场即兴的方式交相呈现,所以节目进行中,时有互相争夺发言权、互抢镜头、相互吐槽破梗,或是互相批评彼此表演笑点不足的竞争场面。或者,时会出现过于无礼的、由戏剧表演的正当性支持,而显得“过于”疼痛的敲头场面之类的“逼真场面”,(我想大家都很明白在闷锅中,某些后辈演员的苦处)。以上这些手法,透过剧场形式与仿真(mimesis)的复原,成为现实的延异,在现实与虚构形式之间拉开距离、形成断裂与安全阻隔,以冲撞美学体制(即共同体)的操控。若有似无地,在收看<全民大闷锅>时我们总可以感觉到,它轻盈了我们沉重的政治意识、转换我们感觉的场景─从政治到娱乐、从苦难到嘻笑─让我们与对同一事物形式的其它感觉与认知得已浮现。闷锅节目公开却隐晦地,藉由每一回每一幕虚构的、多元的戏剧场景,揭示特定形式仍足以产生的变化与新感觉。闷锅电视节目引发的娱乐的政治意识,正像是对在共同体神只庇佑下,因安逸而日益行动迟缓的我们,在感觉或理解事物时的感觉方式僵化、敷衍了事、毫不用心,进行责难。闷锅的拟仿其实揭露了比现实政治形式与政论节目所能带出的,更为真实的共同体困境与恐惧的挣扎。
这样的演出透过电视表演的观点,轻松本然地暴露出─一般政论节目来宾发言之间的争斗共谋、以及追求媒体曝光率的种种媒体机制规则,事实上是表演性的。也就是说,媒体中的个人呈现和表演,在具有主动展演性质的同时。也包含了带出媒体本身结构的性质,此特性在闷锅节目的设计安排中,被露骨地使用。因此,闷锅本身的表演在再现媒体结构以反讽政论节目的同时,它也透过这种表演暴露了整个媒体结构,进而可以反讽之;作为一个讽刺媒体的媒体,其表演不单是对其外部单向的再现而已。也就是说,闷锅的表演与再现、拟仿,甚至主动戳刺了同样附属于媒体结构的自身,它的再现也朝向自己。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闷锅表演的双面性。如同Ranciere所认为的,拟仿绝非是象征性再现的拒绝,而可以是在结构内部进行对结构的破坏、制造断裂。
闷锅最重要的操作与玩笑手法即在于:透过对社会形式、政治现实、人物、事件的扭曲、夸张、变形与幻想虚构,引诱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苦痛、承受(suffering)相异的情绪(,这些受苦来自现有政治形式的僵固带来的死亡,即内在性),即,以笑的形式呈现的愉悦、愤怒、苦恼、罪恶感等等的情绪感觉;并且,同时暴露出:我们(节目观众与全民)对于僵化社会形式的共有与分享, 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共同体之爱。因为同在一起的存续,依赖的是想象共同体的感知能力、与情感的沟通,而不是规训感觉的僵化形式,或是以固定的感知模式观看形式世界。从这里,不难理解某些质疑闷锅节目政治性意义的收视者的危机,因为,他们坚守着对政治事务与社会形式的特定感觉方式,即,固化自身的政治感觉(senses of the political)。闷锅的存在似乎提醒着我们:有时候,过于严肃也不过是某种感觉迟钝,而嘻笑,有时正是一种拉开回视距离的机会。
从全民大闷锅节目播出的 内容 ,也可以发现另一个特色:除了政论节目拟仿之外,它收容各式各样电视节目类型于节目自身之内。节目中穿插陈列的场景式拟仿单元,其场景的设定选择自媒体所热中呈现的场景,以及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所熟悉、感觉亲切且辨识度大的电视媒体节目场景,举凡命理、心灵宗教 教育 、股市 分析 、热门综艺访谈节目、街头选举动员等等;或是虚拟场景,像是知名周刊媒体内部议会、国台办记者会、总统府宴客厅等等。皆欲极尽讽刺玩笑之能事,意图解闷、使人发笑,并且呈现一种嘉年华式的游艺性质,带出台湾民众日常生活中媒体接收的多种样貌。 同时,不仅在他自己内部呈现这种搞怪的异质风格,作为一个电视节目,它以自身呈现这个多音发声的企图。当新闻媒体、政论节目令人厌烦地,一致地重复让人感觉时间错乱,每日上演相同的社会事件报导与政治议题时,闷锅就会突然、不可预期地变回正常、一般的娱乐节目拟仿,甚至其趣味性并不会亚于被模仿的娱乐节目本尊,因为台湾的娱乐节目也往往流于无趣的固定形式。
有时则是反向而行:当媒体一窝蜂炒作某些非关政治现象的事件时,它反而标题反讽道:是不是不谈政治就比较不闷呢?当然,何谓政治并非闷锅要判断与可以判断的;它只是试图维持自身在政治与娱乐之间,作为一个能动性高,变异的媒体中介。即便闷锅仍然映透着一种最基本的资本主义色调,服膺于媒体运作的机制,重视收视率。但是,闷锅与一般娱乐节目不同的价值,最直接的呈现在于:它本身旨在做为某种套脱固定形式的呈现形式,以模仿、以形式的变化、挪用与并置。它在电视节目的社会框架中,积极进行对于形式的创造性实践;正是 Ranciere所指的诗学体制的艺术实践,或是政治美学的实践─做与作的 方法 的积极开展。
“你闷不闷?”这个闷锅持续出现的问题,其实欲求一个相同的回答:“闷!”。这个问题其实是提供一个机会,来向“you”,集体或个别的你,来确认“我们是否在一起”,或是否拥有相似的感觉。如同,相恋的爱人们经常透过提问期待彼此对同一事物有相似的感觉那般。目的是为了厘清对方的感觉,以求能加以沟通、分享对方的情感,以保有“我们”的爱,我们的共同体。 但是同时“你”闷不闷?亦是要问,作为个人的你是否与我们有相同感觉?这隐藏着复数的个人对“我们”的不可能之提问。因为娱乐节目至少是必须满足个人的,所以,当我坐在电视前,面对着以“作假”、演戏、娱乐为名的全民大闷锅时,往往是在期待闷锅节目的演员们要出什么新招,而且是针对个别的我而言的有趣招数。在闷锅每周一到五的播出中,观众其实也不过是面对着那些变异固着、幻想虚构的表演形式等待着、或是期待着他们今天的演出让人惊喜、拍案叫绝。娱乐我们!这其实是困难的任务,因为这好比说要同时满足每一个人不同的需求那样困难。看全民大闷锅时,其实每个观众得到的乐趣,首先,并非是可以说明的。笑的感觉形式呈现,也不一定是基于同样的感觉;反之亦然。笑不一定就代表纯然的愉快。事实上,我们常说笑话,却少有人会刻意去“讨论”笑话,或是分析拟仿讽刺的笑点,因为那只会把一切都搞砸;那不但没乐趣,笑话也不再好笑,并且常常遇到的困难更是在于:你说不出为什么是这个让你发笑,而不是另一个。对笑话的理解,是个人的洞见,也是基于个人在集体的历史里独特的记忆。但重要的是,我们感觉愉悦吗?或是我们的感觉逾越(逾越固旧形式)了吗?
在昆德拉的<笑忘书>当中,他为我们称之为笑的东西,提出了一些深刻有趣的暗示。他提到:
…..当天使们首次听到魔鬼的笑的时候,他们恐慌极了,那是在一群人聚会的餐桌上,一个接一个的天使跟着魔鬼一起笑了起来,足见笑是很有感染性的。 天使知道的很清楚这是对上帝的不敬,是在笑祂所做的那些神奇的事。天使知道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但是自己的能力有限,苦无对策,只好以牙还牙;天使张开嘴,发出了一声不稳定的、呼吸般的声音,是属于他的高音域,且赋予相反的意义。如果魔鬼的笑是意味着万事万物之无意义的话,那么天使的笑便是为世上万物之有条理、构想完善、美好和明智而欢呼。9
昆德拉接着又说:
天使的笑是无比的可笑的,并且如大灾难一般不可思议,魔鬼因而笑得更大声了。但是天使仍然从这里得到了一些别的,…而我们却被愚弄了…全然分不清楚真正的笑(魔鬼的)和模仿的笑(天使的),这两种笑的差别。
这一则故事很容易引起困扰。故事一开始,昆德拉早已经意识到魔鬼与上帝不过属于同一个价值规划的两面,笑当然就不是只有两种或一种的问题。他在此提到的应当是在同一个统治观点上,对笑作为愉悦或是逾越的讨论。因为,在<笑忘书>中,有太多种不同情感所引发的笑;从这足以见得,这里魔鬼的笑是不可全面理解的形式本身。而这正是我们被愚弄之处─我们总以为笑就是愉悦、快乐或是感觉。天使的笑却来自于遭遇了未知的恐慌,而非是对魔鬼的恐惧,而是对不知的笑的恐惧,并且同时是:在这个面对未知的瞬间,天使竟被敌对的魔鬼与它的笑所感染,且天使在此处选择大胆地以模仿魔鬼来维护上帝,以形式的实践罪恶来维护上帝。魔鬼的笑是出神(它本当如此!因为它被设定作为上帝的反面);在无神处笑,既无任何情感也无任何意义,因而也就是某个形式自身,所以那是纯粹的笑、但不是任何表示,或许连笑也不是。而这里天使的笑是模仿,是上帝秩序的界限的暴露,是形式被新感觉投注后的变化意义的瞬间。天使对笑的模仿,是感知与形式的平行并置的瞬间,尚未落入任一方却又同时是分歧岔开的。天使挪用魔鬼的笑作为对抗,魔鬼的笑则是为无意义而笑,是空无,召唤无限的感知向其涌现。
全民大闷锅的形式似乎是呈现为上述故事片段中天使的笑的模仿,可是其并非要维护上帝,而是在试图维护其自身所欲维护的某“美学体制与共同体”的同时,暴露其界限。全民大闷锅并非能超脱于一切美学体制或共同体之外,也并不是完全异于政论节目的一种节目,它并不真的能轻易使我们出神,而是能去企求一个引发如魔鬼的笑般出神的努力。但是出神的瞬间本身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吗?达到未知之空无,即是进入感觉的分配所不是、所不知不准的外部,也就是Bataille所说的他者、至高者(sovereignty)、空无或是共同体,便能中止共同体所暴露的问题吗?有无可能,魔鬼之出神进入的也是神之于我们的不可知处呢?魔鬼那极度空无的笑,难道不带有一丝恐怖的暴力吗?这往往也是全民大闷锅节目所引发的笑,是否具有可以延续的抵抗感觉分配之暴力性,面对其区分、界划、压制排除的问题所在?如果它引发的笑仅仅是带我们进入空无及瞬间消逝,而无法再引起更多的感触、思考与联系的沟通,那么这种笑会不会带来更深的失落?相较之下,一个矛盾自反的天使或许亦有其值得 学习 处。
对不可能避免者的试图躲避,是否是一种逃避呢?亦或是一种生命的努力?也许,它有机会是一种最最低限的,保持在被共有的形式最边缘处、悬置处,可以随时“忘我”与“出神” (ecstasy)的准备。并非忘我或进入不知处本身,而是跳跃前的一个有力踏步、一个姿态,像是一个反拍(抢拍)、半音,或是动作、雕塑、画面上不平衡、不稳定的凝固构图,或紧握着一张正在开奖的彩卷那般,充满动态感觉的稳定形式。虽然不一定能造成流动,但是却可以引发与召唤流动的未来想象,既是机会(chance),游戏、偶然、运气、赌博,也是冒险,伴随着乐趣与遭遇未知的恐怖感。即使,这类乐趣在某些阶段,相当类似我们于共同体内感觉到的愉悦,因为在共同状态的某些时刻里,也可能感觉到一种接近自我死亡却可以立即被激情洗刷的未知。但是,(永远可以但是,并朝向任意方向前进),它总是在祭典上摆出对共同体之神不敬的姿态,毕竟,它是一种向那神、与那沉浸共有认同中的每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你在吗?,然后继续进行原来的游戏的姿态;就像无视于神圣仪式,在祭典里乱跑乱笑或是大哭大闹的小孩一样。
但是,难道那神之于我(个别的人)是在的吗? 难道那神与“我们”是不在的吗? 这种不敬是否是正是由于过于直接暴露、过于贴近于不可抵达的远方的本质,以致虔诚的信徒们常会惊恐地,混杂气愤与罪恶感地制止那小孩;正是由于小孩沾染了神之光辉,所以他们恐惧、忌妒、羞愧。倘若共同体之神只真能现身,能惊奇而不带恐惧地接受此不可能性的,难道不是只有像这小孩的人吗? 这个不敬者的娱乐与游戏嘻笑,往往是自发且无惧的,却也往往被斥为不敬与罪恶(,这里的罪恶必须是在“祭典上”的 而非某些不属于共同体的罪恶,但或许并不存在?!)
转贴于论文网 http://www.lwlm.com全民大闷锅节目并不限定于召唤特定的 政治 情感,(但是它仍可能有这种危险),相反的,它以拟仿的形式、新的形式:扭曲的、极端丑化的、幻想虚构、创造的,来揭露僵化的政治感知界限。在形式中逃离自身,开启我们对政治的感觉能力,即开启政治性(the political);让我们意识到既有现实政治形式的局限性,转向积极的政治形式实践。因而,朝向忘形 忘我 出神,以再不断重新解构/建构共同体。
全民大闷锅虽然不必然每次让人发笑,但是却揭露出政治性与娱乐性之间、 共同体之无效之工与形式的游戏、共同体出神与忘我之间暧昧双重的关联。
它之使我们愉悦,正是因为它所带来的一种轻盈的逾越/愉悦姿态;全民大闷锅是透过对积极的政治性实践,即感觉发配的外在化形式的创造、某种原书写的过程,来达到双向逆反的召唤以及除魅。然而,是否有可能要求一种感觉沟通的能动性,能自在表达个人的真实情感与意见,维持动态变化的特性,而又不被我们藉以表达的形式所裁切限制?
(还可以再问的事是,全民大闷锅对媒体结构的破坏是何种程度?或是,这种藉自我嘲讽以嘲讽他者的过程,对于一般观众而言有怎样的实质 影响 ?观众又如何能避免陷入媒体结构运作的收编伎俩之中?这些,则是必须再探究、再实践的 问题 。)
另一方面,在感觉的分配里,不难看出感觉者与可感者(及形式),存在于同一个问题层次之中。那位在不可感知处统领感觉的共同体,也就是那美学体制,或是先验形式系统,既必须透过“能够感觉者”,即个体的存有或是“主体”,以及,同时,可引发感觉的可感形式,包括物质与外在化、具体化的形式,来实践自身。从这里开始,浮现出第二个问题,即,一个藉由可见形式(必然是复数的),向感觉经验呈现自己的共同体,如何可能确保无数个别的“感觉者”的感知是处在同一个稳定的、非虚幻的“共同体”的共享成分中?并于感觉共同时,又能屈服于其对于个人感觉的分配?感觉的分配,难道仅仅只是像自来水系统那样流通分配我们的感觉吗?难道这些感觉的接受与纾发,不是来自每个殊异不同的肉体或心?因而我们需要补充Nancy对共同体的讨论。
五、不工作的共同体
(一)Nancy的讨论
共同体是向我们发生的某物。对Nancy而言,共同体(community)并不占据空间(taken place),不像那些相异的 社会 形式(social forms)那样。正如Ranciere说的,在共同体(即美学体制)与可见性形式的关系中,美学体制在可感知之外,她只能透过形式向感知呈现自身,而非直接在场,她是不在的在场。
Nancy认为:
在 现代 ,共同体从不曾在社会形式的投影(projections)中占据任何位置。(或许正是因为现代的)Gesellschaft,社会,即力、需求与符号分离的联合,取代了(has taken the place of)某种我们无法名之,曾经运作着比社会联系(social bond)的沟通更为广褒的沟通,与更加穿透、遍布于此联系的分裂;并且它通常包含了比我们期待共产主义低限(communitarian minimum,或是沟通主义的低限?)所能带来的、更为严厉的影响,如:孤绝、排除、训诫、无助。社会并不建立于共同体的废墟之上,而是发生自某事物的失踪或守恒(不灭、保存)。所以共同体并非是社会所击溃或失落者,而是紧随在社会之后,发生于(happens to)我们的那些问题、等待、事件与命令。10
在Nancy的这段话中,透露了某种现代性经验,与我们对共同体的欲望的关联。共同体本身并不是一种痛苦的损失(a loss),更绝不是任何已失去了的,(我们在现代之前也并不曾拥有),或过去的人民精神或机制。Nancy指出,共同体的失落(loss),是情感(与思想)分享、沟通的内在性与亲密的失落,并且,正是这个失落建构了共同体自身11。Nancy说,对这种失落的清醒意识,是内在性(immanence)的临在,将会立即压制共同体或是任何沟通(communication)12。因为在真实中(in reality),内在性所立足之爱的法则、相爱者的死亡(death of lovers)或是个别(the singular bEings)的自杀献祭,是内在性中情感的接合;死亡建构情感的共享状态,创造出此状态中的参与者在他者中拥有自我存续的时刻13。内在性中共有逻辑(logic of communion)的呈现,以殉情的恋人、保护家人而牺牲的个人,或是为神圣理念、宗教、国家、社团自愿光荣赴义的勇士等等社会形式出现。因而,死亡就是内在性的真实(truth)。
Nancy认为14,那些无疑的是为共同体而做的牺牲(immolation),说明这个人类内在性的共同体是一个死亡的共同体:人等同自身于神、 自然 、以及他自身的工作,而一个完整被理解、体现的个人主义个人 是个已死的个人。因为参与共同体的独特的个别存在(singular bEIngs)的死亡,便是绝对内在性;它说明了死亡,(包括它的各种形式),对这个共同体而言,并非有限性(finitude)不可控制的溢出,而是对某一内在生命无限的实践(infinite fulfillment)与欲完成自身的工作。由个别存在的死亡所建立的内在性,召唤共有前来,但她却不曾到来、无法到来,也无法形成未来。形成未来的,仅仅是那些个别的死亡;这种死亡围绕、包裹着共同体,于是,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共同体封闭自成的神圣回路:共有的到来并非死亡。死亡是共同体永恒的过去15,她造就共同体,却必然永远是那失落的、情感分享与沟通的内在性。Nancy指出为内在性而在战争、抗争、或宗教压迫里千万生命的死亡或牺牲,并不会在 哲学 意义中被扬弃:因而,没有辨证,也没有救赎可以将这些死亡引领向任何异于死亡的内在性。Nancy认为死亡与共同体不可分解,而也仅仅只有透过他者的死亡、或是那些共同体的成员的死亡,共同体才被揭露。
共同体因而是不可能执行除死亡以外的任何工作的,因为共同体的出现与揭露,正是对此不可能工作的认识;死亡甚至也仅只有在共同体试图工作时,才会成立。也就是说共同体是不工作的,除死亡之外。16共同体在他者的死亡中被揭露,并且总是透过他者与朝向他者而发生;同时Nancy又说,共同体不是一个自我、本质或是主体的空间,而是总是作为他者的,复数“我”(I's)或“我们”的空间。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他者的共同体,一个我做为其中一份子却又不是我的共同体;所以我们就也是我的他者状态,即我之外于我。
接着Nancy在此处引证出一个特别的理解:既然共同体的出现,总是由独特的个别存有的死亡达成、藉由他者的死亡才能向“我”暴露共同体的状态,即那个作为共同体一部分的、被共有的“我们”或是我之外于我的他者状态,也才会伴随共同体出现。那么就是说,我,即那个独特的个别存有状态,不但是透过我的他者状态的死亡而出生的,也意即是说,做为独特个别的存有,是透过共同体的发生而出现;而其中必须经历他者或我之外于我的死亡。所以,随共同体发生的个别存有,也总会是分歧的,既是我,也是我们即他者。
在对共同体的现代经验里,那清晰的分离意识的迫切,是对个体(the inpidual)位置的一种复返。对Bataille而言,个体是一特殊物(the thing),是外于沟通与共同体的存在(being),但Nancy认为,此种极度清晰的意识是一种在黑格尔哲学意义下,对理解的意识的欲望(consciousness’s desire for recognition)的悬置; 是对无限欲望的有限中断,有限欲望的无限晕厥,也就是至高者(sovereignty)本身:外于欲望的欲望(即断念)、外于自身的自己(即忘我出神,即他者)。所以,此清晰意识呈现为共同体的与他者的沟通,同时是在共同体内所进行的沟通(communication),以及共同体之沟通(communicate)。Nancy说,这个意识或是沟通,是出神;也就是说这个意识从不是“我的”;“我”只能通过以及在共同体内拥有之。
共同体并不拥有或主宰此意识,共同体便“是”此内在性之夜的忘我(出神)意识17。因为作为他者的共同体与内在性根本的悖反。(只有死亡能结合两者) 因而,此种意识也是自我意识的中断。从这可以明白,出神和忘我(ecstasy):一方面是个别存在之不可共享共量的“我”,即出神;一方面是我之外于我的他者状态,即忘我。两者同时是共同体之中对共有的中断,也是共同体自身─共同体抵抗它自己与其每一部分,抵抗形成她自身的所有成分,抵抗内在性。同时,个别存在相近于绝对的内在性,对共同体而言是被动性、承受(suffering)与溢出(the excess)。因而,在共同体里面进行沟通的,是“被解放的”、个别存在(singular being)分享其个别性的激情(passion),而非个别存在本身。个别性(singularity)在此展现为存在(being)的激情。共同体因而是个别存在对沟通的激情的暴露,是灿烂的荣光,是坦露于死亡面前的愉悦(joy before death或),这种愉悦与高潮也应是因为与他者的联系。而,共同体的分享、沟通、共有,永不可能完成;Bataille说了:一个属于那些不具共同者的共同体。即共同体不可能完成自己,却要在互为界限的共同体与出神忘我之间,不断地中断而出现,出现暴露而企求永不达成的沟通,如此这般的流变于此“之间”。
并且Nancy并不认为ecstasy碰触界限(limit),便仅仅是一种中止与悬置姿态停留在难以认识的他者面前而已,而是与Ranciere相似,他们企求一种以不断共同出现(com-appear)的形式在场、外延与创作,在界限上探索与向他者生成联系,也才可能使共同体本身的沟通不致陷入僵硬的死亡工作之中。
从Ranciere美学体制的实践过程,可见性形式本身对此体制(或是共同体)的背叛,到Nancy所展开的,共同体自行解构的本质,说明了情感(或是passion激情)的共有、沟通、共同体,是作为感知者的“我”与共同体的共同出现,是以死亡所建构的矛盾关系。这进一步地补充说明Ranciere的感觉分配里,感觉者与呈现共同体的感觉经验之间的问题。
我们在这些思考中,同时幻见了共同体的白昼与黑夜:可感的可见性的外在化、空间化形式,与共同体之感觉者─“我”的死亡、死亡中的诞生,以及共同体在实践自身时不时的中断出神,自行双重的背叛。我们借着某种感觉性的指涉回返,来理解此种共同状态;在这时刻的共同感必然是朝向我们所展开,并为我们所遭遇。这无可逃避的遭遇,必然是双重的、分裂的,总是因“在此”的深刻孤独而能“共在彼处”的喜悦,亦因结合的压迫而显孤独的自由,或因荣光的面容而显其背脊的晦暗,他既是光也是黑暗,并因为坚实而不可能被轻易消弥抚平的存在状态。
六、出神、忘我:对政治性不断开启的再理解
政治性(the political) 并非仅指涉某种社会治理机制的结构,即我们一般对政治(politics)的认识那样。政治性(the political),实质上,是一个向自身无效的沟通、不断运作、中断自己的共同体。从Nancy那里,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共同体的沟通是个别存在分享的激情;同时,个别性展现为存在的激情。所以个别性的概貌是政治的(political),其沟通与其ecstasy亦是,共同体亦是。政治性的打开是共同体的不僵化。
台湾 政治现象里,那共享的政治激情暴露的,即是,政治性本质正是激情的共享,一个经历自身共享的经验的共同体。台湾民众普遍对政治事务甚至生活事务的激动情感表达,以及沉痛的情绪泛滥,也就不难理解地,这是政治性本质对现实政治(politics)的溢出;或是说,既有现实政治形式已不复能处理应付(cover)政治性的暴露了。这说明,在台湾,政治性界限的确是不断地暴露出来,却无力以情感以外的方式,来进一步建立联系与沟通。此无效解构自身的共同体,恰恰是Ranciere讨论里,政治的美学体制与诗学体制之间的关系。但是,现阶段,台湾社会现象中的失控情感,传达的却是共同体的虚弱状态、或是诗学体制的无力。这导致Ranciere的政治的美学实践,即诗学体制与美学体制之关系的损坏,因为现实政治形式,即其作为(doing and making),不再能有效地向感觉经验呈现美学体制(共同体)。
以致感觉经验者只能以情感的表现本身作为实践的形式,不断生发出对共同体的激情;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这个现象往往以最为直接的展演形式的景观呈现情绪抒发,也可以说明为何这种政治性的,会倾向以最为刻板的、最富光荣传统的、最公开可见、有效益的既有政治形式呈现,或以之为名。僵硬的政治论述、传统圣人的形象再造、动辄街头抗争、情绪性的言说等经典形式,此状况指向一个原因,就是台湾政治现实(politics)缺少了一些对于行动前迫切欲望与情绪的中断与再思考;对这些行动激情的中断并不是某种压制的暴力,而是企求更开放的机会与创造的到来,让我们的感觉不断再流动生成共同体的活络。因此,我们并非要对于自行无效的共同体加以抨击,或是企图要弃置、逃脱于共同体的出现,因为那只会使沟通消失,(我们不能没有她,无论她存不存在),而是要思考:共同体之虚弱问题,以及我们如何自行作为、重新召回护佑我们的神? 似乎,这更是一个传统的,天助自助者的问题。或许。
如果所有感觉的(the sensible),是无限、无秩序的空间(space);那么在一特定场所(place)中(被允许的、被管理分配的、可以)感觉的形式,以及这个场所自身,名为政治(politics),我们对它的期待,永远会是一个空气流通、内部外部空间相通,可以听见、看见、对外呼喊招手,感觉丰富的居所。因而,政治性(the political,被感觉的)的打开,或说,对政治(politics)的感觉的打开,是能够敏锐地感觉、与不断开启流动感觉(the sensible)。因为是感觉让我们理解、知晓、了解与区判与再创造,使我与我之外建立关系,以及共处。她是内在性的对立,(死亡对立于感觉;所以爱不会等于死亡,但他们总是在一起)。另一方面,要能将感觉以充分的形式表达出来,以召唤、铭刻自己,是以坚持共同体的狂喜(ecstasy:可以说,极端的感觉)的自相矛盾,而打开感觉的实践形式,也必须是有所作为,而不仅只是被动,而是要在意义与感觉形式上实践中,获得我们的脉搏。台湾政治的政治性打开。也须如此看待。
(但这个收尾,永远不可能是问题的答案。我们的解答,永远是共同体的解答,必然是永远不只一个的解答,所以必须不断追问与回答。)
参考 书目:
Jacques Rancier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trans. Bagriel Rockhill, London :Continuum, 2000
Jean-Luc Nancy,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trans. Peter Connor et al.,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4. pp.1-42
Jean-Luc Nancy, “the free voice of man”,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Pp.32-54
Bataille Georges,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trans. Allan Stoekl, Carl R. Lovitts and Donald M. Leslie J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笑忘书》,米兰.昆德拉 ,吕嘉行译 ,林白出版社,1988
《欢悦的智能》,尼采 ,余鸿荣译 ,志文出版社. 1988
注释:
P22,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Jacques Ranciere 应异于Foucault的绉褶
P23,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Jacques Ranciere
尤其针对前卫(avant-garde) 艺术 革命之后的艺术与文学史 发展 而言。
p13,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Jacques Ranciere
p179, <欢悦的智能>, 尼采. 余鸿荣译, 志文出版社,1982 ,
在此,我持续无法确定的是,在台湾到底有哪些关于共同体的想象种类?由于我们的爱与认同是如此复杂难解。
亚里斯多德认为,一个公民就是在政治治理(governing)行动与被治理之中,作为一份子(has a part)的个体。柏拉图更进一步认为,这个公民所参与其中的政治体制,是一个由聚集的工艺者(artisans)、不可侵犯的律法书写、与作为机构(institution)的剧场,为基础的民主政体。
p17,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Jacques Ranciere
p76, <笑忘书>,米兰 昆德拉, 吕嘉行译, 林白出版社.1980
p11,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Jean-Luc Nancy
p12, 同上。
p12, 同上。“如果我们思考绝对内在性的达成,以及遗忘无法消灭的个别(singular)的成因,那么共同体或沟通将不复存在,留下的,只会是原子持续的恒等特性(the continuous identity of atoms),保持自身于进行任何变化反应前的状态中…”
p13,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Jean-Luc Nancy。
同上
同上
P15, 同上
p19,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Jean-Luc Nancy
转贴于论文网 http://www.lwlm.com